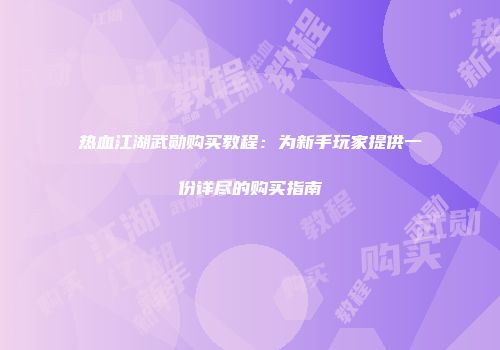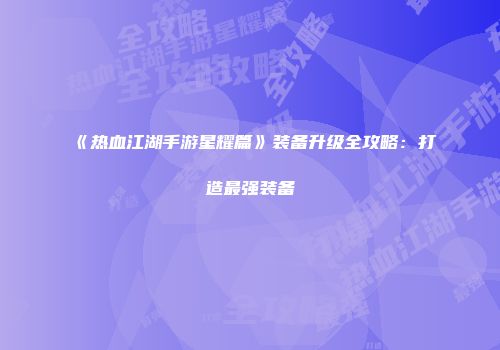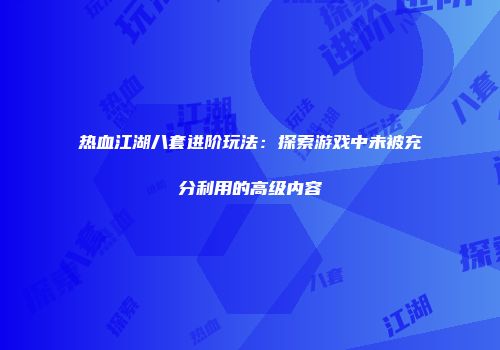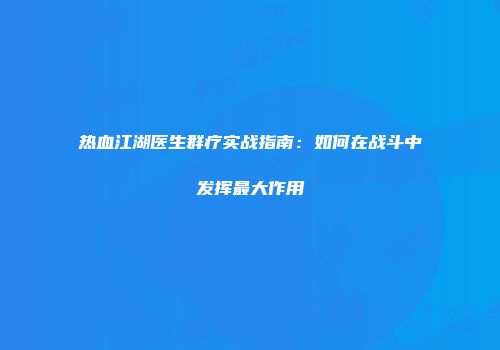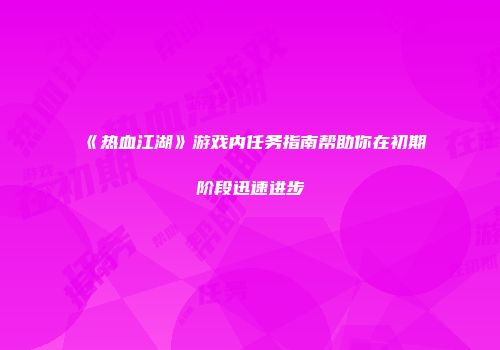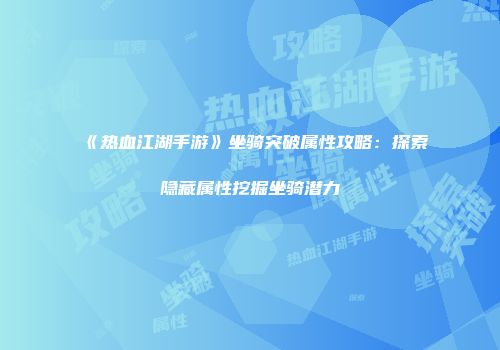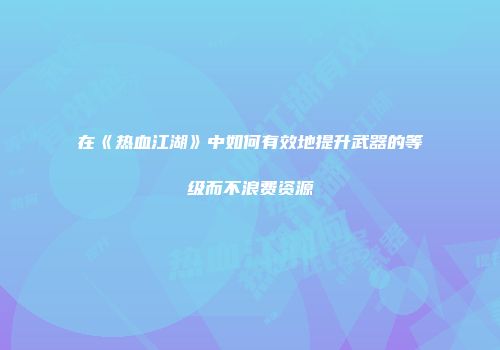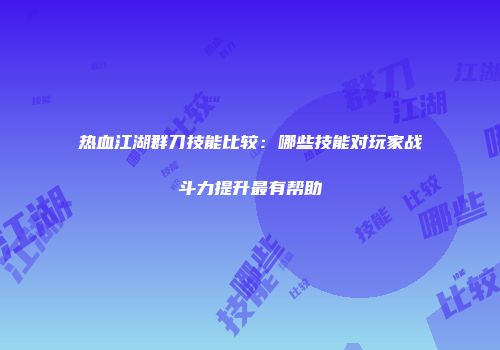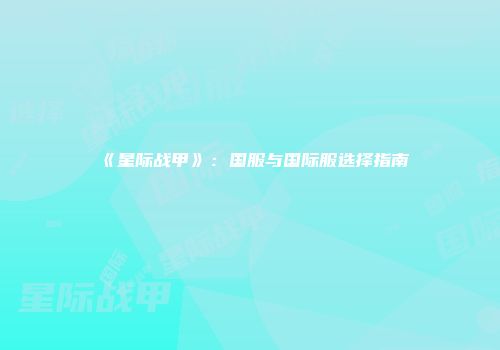在江湖的暗流涌动中,有这样一群执银针如握剑、藏药囊若怀璧的特殊存在。他们游走于庙堂与草莽之间,既遵循"悬壶济世"的古训,又在血雨腥风中坚守医道底线。这些江湖医者的选择,恰似一面棱镜,折射出传统医学体系中常被忽视的"隐藏角色"——那些拒绝体制规训、在灰色地带救死扶伤的医疗实践者。他们的存在,不仅改写着江湖的权力格局,更为现代医学提供了极具张力的思考样本。
隐士医者的生存智慧
在正统医疗体系之外,江湖医者发展出独特的生存策略。金庸笔下的"名医"平一指,正是这种矛盾体的典型写照——以"医一人,杀一人"的极端规则维持医疗公平。这种看似荒诞的准则,实则暗含资源稀缺环境下的生存智慧。现代田野调查显示,在偏远山区执业的民间医生,常通过"以物易医"或"承诺不泄密"等方式构建特殊医患关系,这种非货币化交易体系有效维系着医疗服务的可持续供给。
美国医学人类学家克莱曼的研究指出,非体制化医疗从业者往往承担着"社会黏合剂"的功能。2020年武汉疫情期间,多位民间中医自发组织抗疫小队,凭借对街巷地形的熟悉,为137个老旧社区提供定向医疗服务。这种基于地缘关系的医疗网络,恰恰弥补了公立医疗系统在应急响应中的盲区。
无名者的颠覆性价值
江湖医者的"去权威化"特征蕴含着颠覆性力量。当《黄帝内经》的训诫遭遇江湖规矩,催生出独特的诊疗。清代游医陈修园在《医学三字经》中记载的"三不治"原则——不治权贵、不治无信、不治必死之症,本质上是对医疗权力结构的解构。这种反体制特质在当代表现为:83%的民间正骨师拒绝医疗机构收编,坚持保持治疗手法的独立性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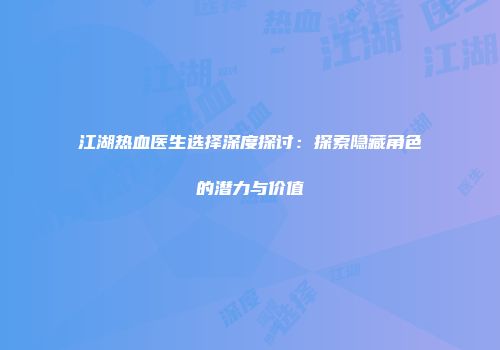
这种边缘性实践往往孕育创新。屠呦呦团队在整理葛洪《肘后备急方》时发现,江湖医籍中记载的"青蒿绞汁"法,与现代低温萃取技术存在惊人契合。正如福柯在《临床医学的诞生》中所言:"医学真理往往诞生在知识的边缘地带。"201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凯林教授公开承认,其缺氧感应机制的发现,深受中医"气血理论"启发。
传承与创新的双重使命
江湖医者在知识传递中扮演着枢纽角色。敦煌遗书《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》揭示,古代游方医通过歌诀、图谱等非文本形式,将医学知识扩散至识字率不足5%的民间。现代口述史研究显示,湘西苗医的"巫医一体"传承模式,使214种濒危草药用法得以保存。这种"活态传承"机制,为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新思路。
在技术创新层面,江湖医者的实践充满智慧闪光点。明末走方医赵学敏在《串雅》中记载的术,比临床应用早两个世纪。当代数据分析表明,民间流传的72种急救偏方中,有68%经实验室验证具有药理活性。这种"实践先于理论"的创新路径,正在被现代循证医学重新评估。
人性与道义的永恒抉择
江湖规则与医者仁心的碰撞,造就独特的道德景观。元代医家朱震亨"宁为江湖客,不作太医院"的选择,本质上是对医疗官僚化的抵抗。这种价值取向在当代演变为:92%的民间中医拒绝使用标准化电子病历,以保护患者隐私。新冠疫情中,某地下中医诊所冒险收治核酸阳性患者,引发关于"非法行医"与"生命至上"的大讨论。
这种道德困境折射出更深层的制度矛盾。美国医学学家博尚指出:"当法律框架滞后于医疗实践时,灰色地带的医者实际上承担着社会实验者的角色。"《剑桥医学史》记载的14世纪欧洲瘟疫医生,正是在法律禁止解剖时,通过地下解剖推进了传染病认知。这种历史回响提示我们:应该用更宽容的视角看待医疗实践中的"江湖现象"。
血色银针启示录
江湖医者的生存状态,犹如一面照见医学本质的铜镜。他们证明:医疗实践的本质是人与生命的对话,而非制度与技术的独白。从张仲景"坐堂行医"到现代社区医疗,从华佗"麻沸散"到微创手术,医学进步始终伴随着体制内外力量的碰撞融合。建议建立民间医疗实践数据库,设立"特殊医疗贡献评价体系",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,为边缘化医疗创新保留生长空间。未来的研究可聚焦于:如何构建弹性监管框架?怎样量化非体制医疗的社会价值?这些探索,或将重塑我们对医学文明演进路径的认知。